阿特新闻
杭春晓:“知识折叠”与历史的“千层酥”——20世纪20年代全球语境中的“传统”与“西方”
时间:2023年02月28日 作者: 来源:美术杂志社
三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亦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因聚会活动主要发生在伦敦市布鲁姆斯伯里区而得名。该区位于伦敦市西区,附近就是伦敦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俞晓霞的研究,对这一文化圈有着较为清晰的梳理:
自1904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哥哥索比·斯蒂芬,把自己在剑桥的同窗带到他位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的家中,进行每周四固定的聚谈会开始,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也由此逐渐形成。在接下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所聚集的名流越来越多,包括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诗人T.S.艾略特、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化界知识精英,因为同窗、知己或是姻亲关系而逐步形成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他们在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上高谈阔论,艺术、哲学、文学、美学无所不涉,对G.E.摩尔伦理学的共同认可,对理性宽容精神的崇尚与践行,使得这群当时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文化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一道令人瞩目的、以知识贵族和文化精英为标识的文化风景线。
聚集在布鲁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对维多利亚时代各种清规戒律颇为不屑。他们倡导新文艺、新理论,践行个性解放的生活,对20世纪思想文化产生诸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特立独行、离经叛道,却强调一种宽容之理性精神。故而,他们的新思想对非西方文化保持了开放性。毫无疑问,这些非西方文化自然包括中国文化,尤其在韦利介入之后。程章灿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常为人忽略,但却是彼时东西方重要的联通纽带。在西方汉学中,韦利对《诗经》《论语》等中国经典的翻译,影响深远。作为宾扬的助理,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也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美术的理解、接受。虽然,韦利并非布鲁姆斯伯里的核心成员,但他无疑为这一群体带来了通往中国绘画的桥梁。尤其,弗莱与宾扬本身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不仅为韦利的《中国绘画研究概论》写过书评,还为宾扬的《远东绘画》写过书评。或因如此,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也出现了某种“中国色彩”。诸如,他对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关乎线条的比较:
毫无疑问,欧洲绘画最初也是建基于线条之上的,同样毫无疑问,现在我们也正在向它回归。但是,在很久以前,这种线条的韵味开始被其他的因素所影响,而且随着我们关于外部造型知识的增加,或者说,当我们在绘画表现时更多地考虑外部造型时,对线条的意味的考虑便越发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中国绘画,即使是在更晚近的和更为成熟的时期——其实,中国艺术在最遥远的古代时期也是相当成熟的——也从没放弃把线条的韵味作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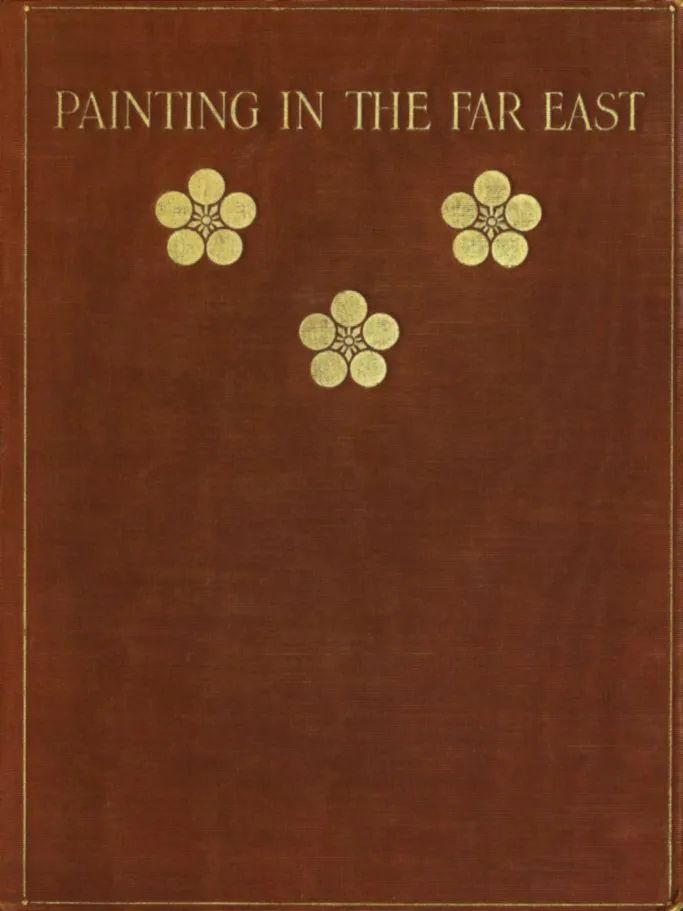
图8《远东绘画》书影
在这段表述中,弗莱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逻辑:中西绘画最初都“建基于线条之上”。其后,西方因造型知识的增加而减弱了线条因素,但中国没有放弃“线条的韵味”。如果将此对比宾扬1904年关乎线条的讨论,我们能够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认知。显然,用线条加气韵的“中国组合”赋予绘画形式某种特别的价值,为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提供了别样的路径。沈语冰的研究表明:弗莱理论的基本形态主要形成于1908年至1912年,之后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此时,宾扬正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推动《女史箴图》及其背后的中国画。鉴于两者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互动”带来了具有关联性的“生产”。在一篇讨论现代艺术的文章《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段》(Line as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中,弗莱使用了“书法式”(calligraphic)这一明确具有中国意味的概念,从而表明“在建构成熟的现代主义理论时对中国书法的明确指涉”。于是,弗莱的“看法”——“现在我们也正在向它回归”,正暗示了某种潜在的“中国影响”。包华石在一篇名为《中国体为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的文章中,根据这种影响,提出“现代艺术的发展原本是跨文化的、国际性的过程”。
将“现代性”从封闭的西方逻辑中解放出来,放在跨文化、国际性的视野中,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进行类似的思考时,我们也要倍加小心:对“中国影响”的发现,不能转向新的“中国中心主义”。也即,在现代性建构史中发现“中国”,是为了打开隐匿在现行叙事中的“褶皱”,揭示历史发生的丰富性,而非建立新的决定论色彩的因果关系。确实,在弗莱理论中找到“中国基因”并不难。正如1910年为宾扬《远东绘画》(图8)所写书评,他对中国画之于西方艺术转型的价值,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褒扬。然而,我们却也不能据此认为弗莱是“中国主义者”,因为他对形式的强调从来未曾脱离其反思西方再现性绘画的基本脉络。应该说,从毕达哥拉斯数理形式到康德之审美纯粹性,西方从来不曾缺乏形式的关注。这类资源,才是弗莱思考的真正基础。诸如他在强调中国画的启发价值后,往往都会对西画发展方向作出判断——“回到自己久已忘却的传统”。
基于此,沈语冰的“担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此而否认“跨文化建构”却不明智。所谓跨文化,亦可称之为全球史观。它的目标是打破区域文化的自我中心,揭示曾经具有的却被“后世叙事”遮蔽的“广泛联系性”。跨文化并非用“新的中心”取代“旧的中心”,而是为了打开隐匿的历史褶皱,找到更为整体化的认知前提。之所以称之为全球史观,是因为跨文化的历史褶皱产生于“区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或可说,区域文化就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且一直受益于全球化而获得发展。如此表述,会让人不解甚至质疑:我们习惯将全球化视作近世以来的现象,区域文化先于全球化,又怎会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但问题在于,全球化是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就开始的进程。当现代人类的祖先以每年50米速度迁移时,人类便开始了广义概念上的全球化。只不过,受制于迁移的速度,全球化的早期形态与今天不一样。正如一条河流,水流过慢时会产生沉淀现象。早期全球化在交通、信息传播等交流速度的限制下,产生“沉淀现象”,并因此形成区域文化,也即区域文化是全球化在“交流速度小于沉淀速度”时出现的特殊现象。近代科技改变了交通与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交流速度”越来越大于“沉淀速度”。与之相应,区域文化的沉淀效应就越来越弱。是以,区域文化与全球化是一种伴生现象,其显性或隐性取决于“交流”与“沉淀”的速度比:当“沉淀”大于“交流”时,区域文化的传统成为显性,全球化相对隐性;反之则全球化成为显性,区域文化相对隐性。
古典时代的交流手段落后,“速度效应”偏向“区域文化的显性”,但并不代表全球化不会发生作用。伴随看似舒缓的商业流通与人口迁移,区域文化不断地从隐性交流中得到资源补给。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各类交流手段获得快速发展。与之相应,“速度效应”越来越偏向“全球化的显性”,直至网络时代的地球村。然而,这也不意味着区域文化不再生效,基于历史沉积及人口聚居在空间上的距离,即便高速全球化的今天,区域文化的沉淀仍在持续,哪怕相对比较微弱。正因为仍然存在区域沉淀,今天的“全球化”才会得到持续性的资源补给,而非单一因素控制下的“封闭”的全球化。所以,“沉淀”与“交流”的共生,不仅在过去保证了区域文化处于开放状态,也在今天保证了全球化的开放状态。基于如此视角,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整体历史”犹如绵延交织的海绵体,充满了相互贯通的管道。诸多不为重视的细节中,存在大量被后世主动或被动遮蔽的“事件”。“XX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正是这种遮蔽带来的结果。因此,历史研究发现这些“相互贯通”的细节,是对“XX中心主义”展开的一场认知漫游。正如包华石提出的问题:“现代性”作为民族主义产物,如何在历史建构中屏蔽了“非民族文化基因”?提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为了讨论西方现代性所受到的中国影响,莫不如说是为了检讨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因此,现代性的“中国基因”不应理解为新的因果关系,而应被看作隐匿的“历史褶皱”,是被后世“必然性”忽略了的“偶然性”。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须剔除“后世眼光或放大、或遮蔽而带来的‘价值判断’”,将其还原为历史本就存在的丰富与复杂——历史的千层酥。唯因于此,视弗莱理论涉及的“中国基因”为新的决定因素,势必会掉入新的“XX中心主义”陷阱之中。正确判断弗莱理论中的“中国基因”,不仅帮助我们避免新的“XX中心主义”,也让我们更为轻松地作出判断:弗莱的“中国”并非原本意义上的中国,而是被弗莱的认知路线选择、转译,甚至是误读的“中国”。亦如宾扬在《远东绘画》中提及的宋代绘画,基本都是南宋风格,表明他关于中国画的知识并不全面。
除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画,宾扬有关中国画的知识,主要源自冈仓天心和高桥健三创办的《国华》杂志,但这并不影响他从自己的立场来理解中国画。基于宾扬本身就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他对中国画的讨论自然地与“现代”这一新兴概念发生了关联。《远东绘画》第九章“中国宋代”的开篇,正是通过“现代”一词,引出宋画:
实际上,我们用现代这个词暗示什么?在我看来,一个现代的时代意味着民族间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已然被超越:人们的思想表现为自由的状态,并因此获悉生命的意义,可以公正地评估外界的影响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再是持械相战的状态,转而文明且优雅。如果我们从宋代留存的艺术品中判断,它显然具有这种现代特征。
现代诗人宾扬对中国古典时代的“解读”,明显带有自身文化反思的逻辑。至于中国宋代是否具有这种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类似的看法形成,就会成为“知识”,进而推动西方产生某种有趣的关乎中国的误读。作为宾扬好友的弗莱,显然接受了这种误读性的“知识”。在弗莱看来,从宾扬认知中获悉的中国宋画与现代性的关系,与借助中国文人画的线条建构现代艺术的形式美学,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是“中国画”的组成部分。殊不知,宋画与文人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谱系中,却是截然不同的美学范式。这种“忽略”,与韦利将荆浩视作南宗绘画的“误读”,异曲同工。究其缘由,正是弗莱、韦利乃至宾扬面对的中国画,并非整体意义上的知识谱系,而是他们因个人机缘所接触到的中国画知识。这种知识以局部化、碎片化的方式被重新理解,并架构出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他们无须对中国人的“认知”负责,而只对自身的“描述”负责。应该说,有关中国画的知识在这一阶段之所以被关注,多少与西方艺术家检讨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传统有关。《远东绘画》中,宾扬在介绍郭熙的画学思想后,将其比作“印象主义”,并辨析了它不同于西方科学印象主义的地方:
这种呈现方法,可谓是我们今天的印象主义。但是,我们必须对东方的印象主义与欧洲印象主义加以区别。欧洲的印象主义仍植根于科学之事实,并以此证实我们无法即时看到任一场景的所有细节,只能聚焦于一个视点之上。若要呈现整个视野之内的全部细节,诚如拉斐尔前派的画面一般,我们的目光就必须在不同的视点中游走。这种述求于科学之权威,而非艺术自身原则的追求,恰是19世纪欧洲艺术的特征。然而,如此述求却不见于中国画家的思想中。他们的理论是将山水画视作艺术家内心情感的表达手段,并因此而自然生发。除了自己的心灵,其它无所重要。真实,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艺术家所寻之生命存在,仅是领悟其自身灵魂。
从印象派的视角看待中国画,也见于韦利关于荆浩的评述。然而,荆浩的作品与《远东绘画》中南宋风格为主的宋画,在中国语境中却有着较大区别。无视它们的差异,统一以印象派“比拟”,亦如弗莱“忽略”宋画与文人画的差异,表明当时的西方汉学对中国画的关注,还相对“粗糙”。抑或说,他们不需要深入风格史展开精细辨析的“中国画”,而只需要一个相对西方存在的“他者”。只要能在这个“他者”身上找到不同于“科学之权威”的“艺术自身之原则”,他们就可以借此检讨“19世纪的欧洲艺术”。显然,无论荆浩、宋画或是文人画,来自远东的中国画都是一种主观绘画,整体上都不具备科学的权威性。那么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用西方印象派概念加以“比拟”便显得如此“理所当然”。因为“印象”(impression)一词,蕴含了某种与客观科学性相对的主观经验。从某种角度看,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艺术,出现了一种内在逻辑:反思文艺复兴以来基于科学而建构的再现性写实风格。虽然印象派绘画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科学主义——对19世纪光学发展的一种回应。但毫无疑问,它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之视觉真实的“真实”,可以被视为主观化的“印象”,并在画面中被表现为看似与物象无关的笔触性色彩、线条与块面。这一特点,在塞尚的手中被进一步放大,乃至弗莱敏锐地捕获到一种“变革”:脱离物象的绘画形式,具有自我的表达功能。或因于此,塞尚在弗莱的艺术史框架中便具有了一种伟大的转折价值。他在1910年翻译法国画家、评论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的《塞尚》一文时,便曾断言:塞尚是“伟大的和原创性的天才……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运动,现时代最有希望、最有成果的运动”。
以形式主义检讨再现性写实传统,使天然带有主观性的中国画成为一种具有辅证价值的参考对象。是故,宾扬、韦利等人的中国画研究恰逢其时地成为弗莱“构想”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礼物”——来自中国的“资源补给”。哪怕他们关乎中国的认知并非全面,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却不会影响“中国基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介入西方现代主义的“知识生产”,并形成“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相互“兼容”的思考模型。有趣的是,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关乎中国传统的“看法”,基于20世纪“全球化”机制而回传中国,影响了中国这一区域文化对自身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判断、选择。在众多全球化的沟通路径之中,1921年蔡元培的“访欧”成为中国美术界接受最新“资源补给”的“事件”之一。甚至,基于蔡氏所具有的权力、影响力,该“事件”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美术界的“历史结构”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