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新闻
杭春晓:“知识折叠”与历史的“千层酥”——20世纪20年代全球语境中的“传统”与“西方”
时间:2023年02月28日 作者: 来源:美术杂志社
一
美术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现实功利的直接能力,故而在五四运动中,多为人所忽略。只有蔡元培因其美育思想一直保持着介入美术活动的行为。职是之故,当他因战后欧洲之现实而重新审视曾经的“西化”之路时,反而不像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那样遭遇反击。在美术之局部场域,蔡氏之文化转向悄然发生,虽无五四运动之波澜壮阔,却平滑而顺利:
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料。此种状态,在各种文化事业,均可见其痕迹;而尤以美术为显而易见。
吾中国之美术,自四千年以前,已有其基础;至于今日,尚能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其间固尝稍稍受波斯,希腊,罗马诸民族之影响;而以二千年前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为最大。自建筑雕塑图画音乐以至日用文饰之品,殆无不有一部分参入印度风,而仍保有中国之特色。故美术日形复杂。至近今数十年,欧洲美术渐渐输入,其技术与观念,均足为最良好之参考品。是以国内美术学校,均兼采欧风;而游学欧洲,研究美术者,亦日盛一日。
研究美术之留学生,以留法者为较多,是以有霍普斯会与美术工学社之组织。其间杰出之才,非徒摹仿欧人之作而已,亦且能于中国风作品中为参入欧风之试验。夫欧洲美术参入中国风,自文艺中兴以还日益显著;而以今日为尤甚。足以征中西美术,自有互换所长之必要。采中国之所长,以加入欧风,欧洲美术家既试验之,然则采欧人之所长以加入中国风,岂非吾国美术家之责任耶?
这是蔡元培1924年为《中国美术展览大会目录》所写序言。若将它和1918年北大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的演讲比较,蔡氏对中西美术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中国画与西洋画”在1918年是二元关系,至1924年则变为“世界之民族文化”。“一民族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意味着将中西放到了一个统一的大结构(世界)中。这种思考模型与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中西问题的反思,颇为相似。中西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成为共同结构(世界)的组成部分。诚因如此,同样提及“采中国之所长,以加入欧风”(西洋昔者已采用中国画法者),“结论”却不再相同:1918年的蔡元培用“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推导出“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强调“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图2);1924年的蔡元培用“欧洲美术家既试验之”,则推导出“采欧人之所长以加入中国风”,强调“仍保有中国之特色”。基于此,蔡氏1918年的武断——“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到1924年,就变成了“吾中国之美术,自四千年以前,已有其基础;至于今日,尚能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1918年的“非”“即”之类的绝对判断,转变为1924年“尚能”一词所引导的“保其固有之精神而不失”。显然,关乎中国传统美术的判断,蔡元培发生了明确之转向。

图2 1918年春季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一、二年级学生在上海龙华地区“野外写生”,丁悚摄

图3(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中国画 24.37cm×343.75cm 5世纪到7世纪 大英博物馆
这种转变,毫无疑问与蔡氏1921年访欧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这次访欧,他不仅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共享了欧洲的新思想,更在美术领域获得了来自西方的“反馈”。该年5月9日,他在大英博物馆“遭遇”宾扬(Laurence Binyon)的研究对象——《女史箴图》(图3),同时还从罗遂斯坦(William Rothenstein)教授那里获得“中国图画之优美”的赞誉。诚如在美国演讲时所述,此次访欧不断碰到西方学者试图从东方寻找思想资源的现象。1921年访欧对蔡元培而言,仿佛是在西方的“东方镜像”中重新确认了“中国”:
(5月12日到达爱丁堡)参观美术学校,晤其校长,询中国学生是否习西洋画,答以有之;彼言中国旧画甚美,万不可破坏。告以分途并进,各不相妨。
如此一幕与张君劢考察德国中学时的所遇,何其相似。今天,我们很难判断蔡元培、张君劢等人在欧洲碰到的类似之“东方镜像”,到底是彼时所遇之人的礼貌性回应,还是坦诚的认知反馈,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毫无疑问,他们在战后欧洲的“所见”“所遇”,确实成为实实在在的“建构力量”:无论伯格森、斯宾格勒等精英思想中蕴含的某种东西方之价值重审,抑或学校、博物馆等诸多微观情境中的东西方之评判话语,共同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信息之网”。身处如此网络的“中国人”,带着“东方”的预设身份与西方的“东方镜像”发生碰撞、共振,进而重塑了自我确认的新方向。
值得警惕的是,指出西方的“东方镜像”对东方人的自我确认产生影响,并不能将其放大为整体性的东西方对话关系。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此信息网中的“镜像”,并非整体性判断,而是个体遭遇的“局部看法”。甚至这些看法的产生也不排除某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误读。诸如宾扬对中国美术的研究,虽较过去获得极大推进——开始改变西方对中国美术的看法,但它并不意味着西方在整体上改变了关乎中国美术的看法。西方对中国美术的“重新认知”,直到今天仍然还在发生的过程中。因此,蔡元培看到的《女史箴图》只是大英博物馆中的《女史箴图》,其蕴含的价值评估,并非欧洲文化系统的整体评估。也即,面对战后欧洲思想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不能将其放大为整个西方与整个东方的“关系”,而应还原为具体的历史参与者的个体经验,进而辨析这种“经验”又是如何渗透到“整体场域”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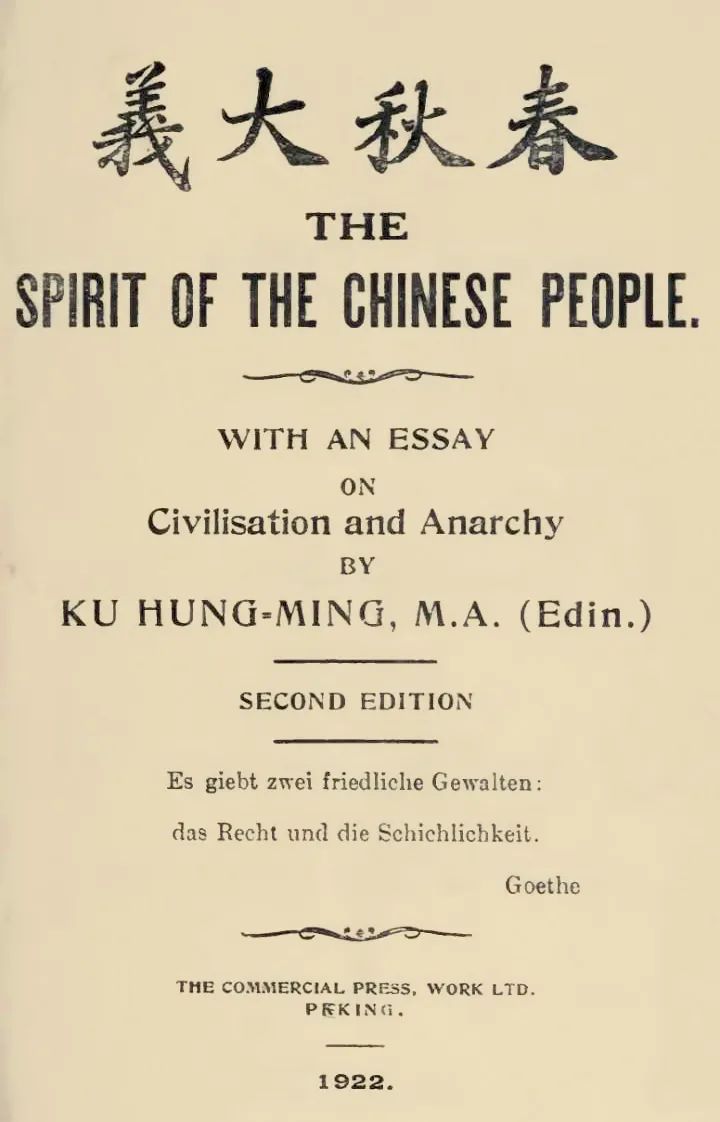
图4 1922年版《春秋大义》书影
显然,从个体角度审视东方、西方的关系,须反思、检讨今天仍然流行的“冲击——反应”论。所谓“冲击——反应”,是将东西方视作宏观结构的二元。它们的关系是假定的两个“文化主体”在整体上相互作用。问题在于,历史上从没有出现如此之“文化主体”间的互动:一个代表“中国”的巨人和一个代表“西方”的巨人,在交互中发生各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理解”是后世研究出于叙事需要,在逻辑上添加的结构——用于完成某种框架性的表述。因此,中西的宏观二元关系只是叙事的技巧,而非历史本身逻辑,更非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判断方式。一旦将这种“后见之明”的结构视作历史的发生逻辑,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中西交流的“文化主体”,都是以个体化的方式完成。处于中西结构之间的具体参与者,从不曾整体地把握自己所代表的文化以及自己所面对的文化。在中西交流的具体事件中,参与者掌握的知识,往往带有个人化的微观逻辑。他们不曾代表封闭状态下的“中国”或“西方”,只能代表独特的认知路径所掌握的、消除了整体性的关乎“中国”或“西方”的局部知识。因此,就中西交流之具体发生而言,历史参与个体就是局部知识混合而成的“或中或西”的“文化主体”。
正如一战前后关于中西文化的检讨,除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外,被视为“保守”之最顽固者——辜鸿铭,恰是或中或西之“文化主体”的最突出代表。民国时仍留着辫子,崇尚缠足、纳妾而被骂作“老怪物”的辜鸿铭,1915年在北京出版了一本用英文写的书——《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图4)。该书以“真正之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为题阐释了“中国人之精神”,其后又辑录了一些文章,包括一篇涉及时政的文章——《战争与出路》。他在该文序言中提出:欧洲文明濒危之际,研习中国文化有助于解决全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一观点早于斯宾格勒的“欧洲文明濒危”,可谓震耳欲聋之“发声”,在当时欧洲亦曾有所影响。但有趣的是,看上去纯粹的中国文明捍卫者——辜鸿铭,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混血儿。
对中国认知不算深刻的“辜鸿铭”,成为中西互动中最具典型性的符号。这看似荒谬的历史细节,直观地展现出:文化交流往往由并不具备宏观代表性的个体完成。所谓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正是由大量“辜鸿铭”这样具体参与者组成的巨大而绵延的“网络”。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认知路径”穿梭于中西之间,以“或中或西”的局部认知形成个人“折叠”。“中”或“西”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宏观意义上的“文化主体”,莫不如说是用以完成个体化“知识折叠”的材料库。无论代表自己的母文化,还是面对异域文化,他们都存在着因个人认知局限而带来的片面性。
强调“习研中国以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之问题”的辜鸿铭,对“中国”的理解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亦如其对旧时陋习的迷恋。但这种“片面性”,未曾影响个体化的“知识折叠”,并最终在中西互动的网络中发出声音,参与塑造了彼时之“中西互动”。辜鸿铭如此,邀请辜氏来北大的蔡元培,亦然。站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路口,个体参与者没能力代表“中国”以面对“西方”。无论是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对“西方”的接受,都无法摆脱个人生命轨迹与各类知识触碰的“线索”。也即,无论“中国”的知识还是“西方”的知识,都没有以整体状态向个体参与者开放。真实的情形是:有关“中国”的局部知识与有关“西方”的局部知识,在个人维度中展开了各具差异的“折叠”,并形成个体化的认知序列。一个时代的“中西互动”,正是由众多的“认知序列”交织而成的轨网络,并非先验之“中”与“西”在整体上发生“冲击——反应”。这一网络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会基于自身认知序列向整体网络释放“个体声波”,以寻找相似频率的“他者”形成“共振”。于是,异彩纷呈的时代之网中,各种“共振”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地推动着网络波动,并最终叠合成时代整体之“声波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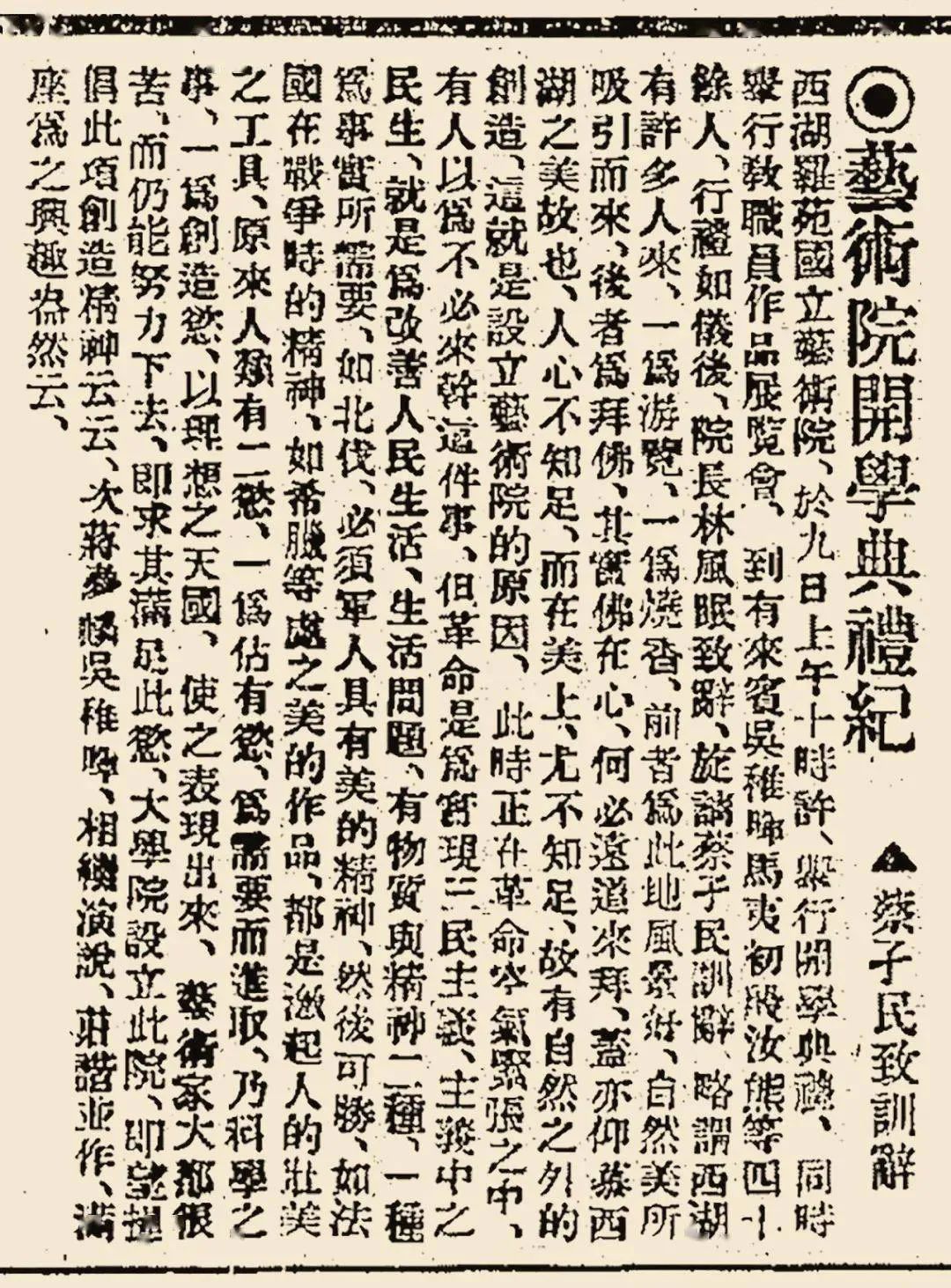
图5 《艺术院开学典礼纪》,载《申报》1928年4月11日
后世研究,针对这种“声波景观”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原因在于:网络中的共振现象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共存。不同角度自然会放大不同波段而得出不同的“描述”。不仅后世研究者如此,即便彼时的参与者亦如此。甚至作为亲历者的时人,身处如此网络中,也容易因自身既有之经历与知识而选择个体化视角,然后做出相应的判断、选择。有些个体,因自身“声波”而排斥不同频率的声波,形成一种“固执”的文化姿态;有些个体,包容不同于自己的“声波”,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姿态。这两种姿态与彼时文化观之“新”“旧”无关,而是带有个体特性的认知习惯。正如1920年前后,“新派”有偏执己见而选激进革命之路者,如陈独秀;“旧派”有接纳异己而选温和改良之路者,如梁启超。蔡元培,大致属于“新派”之开放者,道路选择具有机动、务实的灵活性,亦如蔡氏办学风格所显现的“开放包容”之特质。
将北大校园同时开放给辜鸿铭与胡适的蔡元培,不是自我封闭的“人”。抑或因此,从晚清参加科举到民国执教育之牛耳,他一直处于某种变化中,并因此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序列”。1921年访欧对蔡氏而言,恰是又一次的“自我调整”。当在战后欧洲的“所见”“所遇”中发现新的方向时,他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关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他不再坚持1918年“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的观点。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在1928年西湖国立艺术院成立的演说中(图5),蔡氏将科学与美术进行了清晰的“分离”。应该说,1928年为支持林风眠办学而作的演讲,与1924年发现林风眠时为“中国美术展览大会”所写的序言,内在思想脉络是连贯而一致的。所谓“为科学之事”的“物质生活之占有欲”必然引发“社会之战争”,导致社会之“紊乱不堪”,正源自他战后欧洲之行的所感、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