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新闻
重拾欧班夫人的晴雨表——“真实效应”与现实主义细节批判话语
时间:2022年04月06日 作者:徐蕾 来源:文艺研究
巴特提出的“真实效应”在现实主义诗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巴特将现实主义置于西方文学“逼真性”传统与20世纪60年代方兴未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下,其视野跨度与学理深刻性远非先前的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家所作的印象式、臧否式批评可以比拟。他提炼出的“真实效应”一方面深化了雅各布森对“逼真性”与19世纪现实主义关系的考察,另一方面亦回应了聚焦现实生活的细节性描写为何逐渐失去意义的追问。其次,“真实效应”成为巴特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结构主义批判的概念依据。在《真实效应》发表两年后,巴特在《S/Z》(S/Z: An Essay, 1970)中进一步论证,不仅无用的细节在意指真实,现实主义本身也是“符码上覆盖符码”18,其意指的终点“不管回溯到多么远,起源处只是且总是一种已被写过的真实,一种用于未来的符码,循此可辨清者,极目所见者,只是一连串摹本而已”19。更为重要的是,“真实效应”揭示出现代主义遭遇的符号解体问题早已潜伏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这挑战了彼时西方学界解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对固化的思维定式,为语言学转向后表征危机下的现实主义美学的重大转折拉开序幕,“代表了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范式转型”20,成为当代现实主义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节点。
二、摹仿论的传统:必须保卫的晴雨表
然而,站在21世纪回看“真实效应”的立论依据,人们不禁疑惑,欧班夫人的晴雨表真的仅是在意指真实吗?有没有结构主义符号学之外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难道将细节指认为无用、冗赘、指涉幻象便完成了对晴雨表的盖棺定论吗?诗无达诂、文无达诠,巴特的经典解读也概莫能外。
至少,西方摹仿论的坚定维护者很难认同巴特对现实主义指涉幻觉的符号学解构,他们坚信文本不可能全然与外部世界绝缘,拒绝词语的意指功能对亚里士多德“可然性”(probability)概念的间接否定。站在摹仿论源头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已言明,诗人依据可然性原则组织情节,通过表现“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21,让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变得真实可信,展现具有普遍性的真实,甚至比历史更富哲学性与严肃性。而巴特的“真实效应”宣称,摹仿的语言不仅与真实世界无关,而且向读者刻意隐瞒了这层早已切断的联系,赫然站在了西方经典美学理论的基石——摹仿论——的对立面。对此,高举新摹仿论旗帜的牛津大学教授纳托尔(A. D. Nuttall)指出,现实主义艺术家运用“基于经验的假设”,以“唤起我们全部的人类力量与能力”22,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有赖于对真实生活特征的精准描摹,欧班夫人的晴雨表便是基于经验假设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一处陈设。纳托尔为晴雨表辩护道:“晴雨表并没有自称‘我是真的’,而是在说‘我不就是你在这么一个房间会发现的那种东西吗?’”23事实上,晴雨表在家庭内的存在典型得乏味,与其说它指向真实,不如说指向19世纪人们对中产阶级日常家庭生活空间的共识。
《摹仿论的秩序:巴尔扎克、司汤达、奈瓦尔、福楼拜》的作者、剑桥大学学者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认为,巴特对晴雨表和《淳朴的心》中的其他物品进行区别对待,首先没有尽到符号学阐释的本分。巴特在《真实效应》中对出现在晴雨表下方的钢琴和旁边的纸盒进行了适当的符号学解读,认为它们意味着“资产阶级地位的标志”和“混乱或家道中落的某种标志”,而面对相对未充分编码的“令人担忧”甚至“臭名昭著”的晴雨表时,却“略带悲观地”放弃了把握“它的符号学幽灵”,全然不顾“福楼拜笔下的诺曼底的天气缺少变化到无聊的程度,晴雨表的含义可以被读作对庸碌人生的意指”24。与此同时,晴雨表被巴特挑中做靶子既不合情,也无道理。“相当卑微的、可能完全不会被人注意的”晴雨表被批评家着意升格为焦点,并设定为福楼拜小说中“一个有着相当干扰性的标识”,这一做法被普伦德加斯特比喻为“用符号学的大锤敲打一枚小坚果”25,不过是“集中了符号学的炮弹和修辞的兵力、以对付一场假想战争中的想象敌人而已”26,因为在摹仿文本及其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默许的语言游戏约定,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发现”(anagnorisis)就是这种摹仿语言游戏的构成法则之一27。因此,巴特费心戳穿的指涉幻象其实根本骗不了任何人。换言之,如果有任何幻象的话,它或许只存在于巴特自己的眼中。
致力于深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书评人伍德(James Wood)在《小说机杼》(How Fiction Works, 2008)中驰援了普伦德加斯特的看法,认为巴特对晴雨表的判定“失之草率”28。伍德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确制造了大量冗余、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可这么一层不搭界的细节是真的像生活”29,由此散发出的随意性恰恰呈现了“现实本身自带的一种无关性”30。简单来说,“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没法解释或者毫不相干的东西,正如那个毫无用处的晴雨表,确实存在于真实的房子里”31。伍德承认,文本中虚构的现实的确由许多“效果”构成,但现实主义在效果之外依然可以是真实的,只因“巴特对于现实主义有一种敏感的、欲杀之而后快的敌意”32,才会片面解读晴雨表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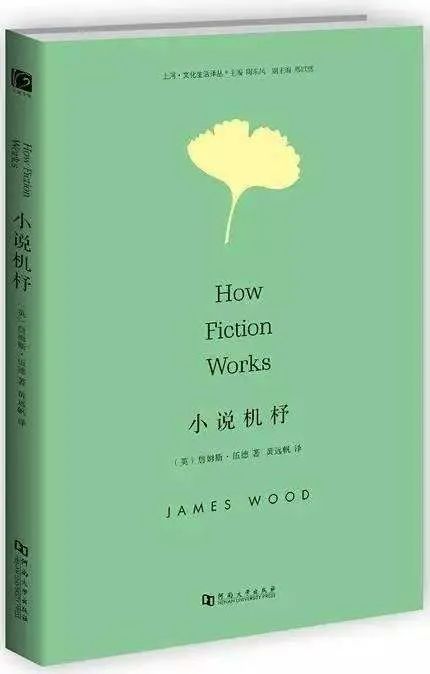
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如果说欧班夫人的晴雨表是巴特攻击现实主义“逼真性”的头号靶子,为晴雨表辩护自然成为摹仿论追随者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强调晴雨表与现实之间的纽带,还是凸显读者与摹仿式文本之间的契约关系,围绕晴雨表的“攻”与“守”背后的实质,是反摹仿论与摹仿论之间旷日持久的交锋的一段现代插曲34。
三、阅读的方法论:走进社会与物质历史的晴雨表
另一种批判符号学解读的路径是改变阐释的语境与框架,在新的诠释域中发掘晴雨表作为物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并不纠结于晴雨表是否指向真实的物质世界,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文学叙事不再被视为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映射,取而代之的是,“文本将现实拉入自身的结构肌理”,从而“让语言能够承载现实自身固有的或者内在的次文本”35。借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作品本身不再被视为外部历史的反映,而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36。循着这一思路,要想理解嵌入文本世界的现实事物,詹姆逊提出解读文本的同心圆式的三层解释框架:政治历史观的、社会观的、历史观的37。具体落实到如何解读欧班夫人的晴雨表,其前提必然要求将物重新置入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也正是詹姆逊1985年《现实主义的房屋平面图》一文的出发点。他在这篇文章中以19世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去神圣化”(desacralization)时刻为锚定点,重新阐释了欧班夫人房屋的区域划分与空间布局对刚刚出现的资产阶级新世界的隐喻,力图突破巴特对晴雨表的符号学解读。詹姆逊以退为进,认为晴雨表绝非“空洞的符号”,其实可以做象征的和图像学的解读。作为一种现代测量仪器,晴雨表“标记了科学与测量对古老的循环与定性式季节时间的胜利”,被隐含在19世纪科技发展与世俗化进程中,一方面凸显了早期资产阶级采取的文化革命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与近旁壁炉架上的罗马灶神庙造型的座钟一起,共同表征了“时间理性化和现代劳动过程管理的主要推手”38。
詹姆逊的解读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导下研究者贯通文学形式研究与政治批评的经典范式,但在“物论”(thing theory)首席理论家布朗(Bill Brown)眼中,将物自身的历史排除到历史分析的图谱之外显然流于粗陋,难免出现漏洞。布朗在《物质无意识》一书的“导论”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巴特还是詹姆逊,都没有考虑到晴雨表自身的物质属性。詹姆逊想当然地认定晴雨表被放在钢琴上,将它视为法国人维蒂(Lucien Vidie)1844年申请专利的新式无液气压计,但这一设定却难以得到文本内部的印证。一方面,小说此处原文为“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匣子、纸盒,堆得像一座金字塔”39,布朗指出,“如果它在钢琴的上方,就一定悬挂在墙上”40,乃是旧式的水银晴雨表;另一方面,小说虽然发表在1877年,但故事描写的欧班夫人的房子却是在19世纪初装修的,彼时新式晴雨表尚未问世,因此它不符合故事的年代设定。布朗注意到,《淳朴的心》发表时,维蒂和他的新式晴雨表已为人们熟知——这种新型测量仪不仅在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拿过奖,在维蒂的专利过期后,仅法国巴黎的一家公司在1860—1866年间就售出了两万件新式晴雨表。布朗据此认为,当福楼拜的读者看到这枚老式晴雨表出现在欧班夫人起居室里的时候,他们内心隐隐感慨的或许是“资产阶级文化资本的过去”,而不是19世纪产业技术和科技的进步,作为测量工具的旧式晴雨表凸显出的更有可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41。同时,纵观小说,女主人公费莉西泰(欧班夫人的女仆)的人生意义浸润在她的物质世界中,镶嵌于被虫蛀的绒帽、鹦鹉的标本等物品之间42,并推动她把欧班夫人夭折的女儿、宠物鸟的魂灵等缺席之物化身为“可被感知的、生机勃勃的在场”43。布朗对福楼拜小说中物化世界的解读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詹姆逊在小说中锁定的“去神圣化”时刻。

比尔·布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