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新闻
陈嘉映:从作品到文本
时间:2022年04月06日 作者:陈嘉映 来源:森雅艺术馆

所谓阐发、引申,我是指通过逻辑、想象力等说出作者不曾说却会说的,而不是指从某句话引发出来的感想。阐发庄子和从庄子兴发是两回事。前者要求对庄子的思想系统有相当的把握,后者用不着那个。我引用一句庄子来加以阐发某种思想,后来证明这句话不是庄子的而是后人窜入的,这段阐发就失效了。我若引用一句庄子然后发了一番感想,后来证明那句话不是庄子说的,这并不影响我那番感想的品质。我的想法并不依托于庄子,庄子只是一个兴的由头,借它来兴,就像借草木鱼虫来兴一样,就像借其他醒目的事物来兴,因了它的显著、因了它的众所周知。阐发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感想则是以感想者为中心的,他引用他人是一种修辞手段,他所引用的东西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发感想和解释没有什么关系,不幸,我们这个时代通常把发感想认作解释的主要方式。
一般说来,阐发以考据和释义为前提。但阐发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考据工作也是参照释义甚至文本的现代解释进行的。
创新。按说,创新和解释是两回事。但,有没有凭空而起的思想创新?为什么很多新思想声称自己是对旧思想的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把思想创新和解释问题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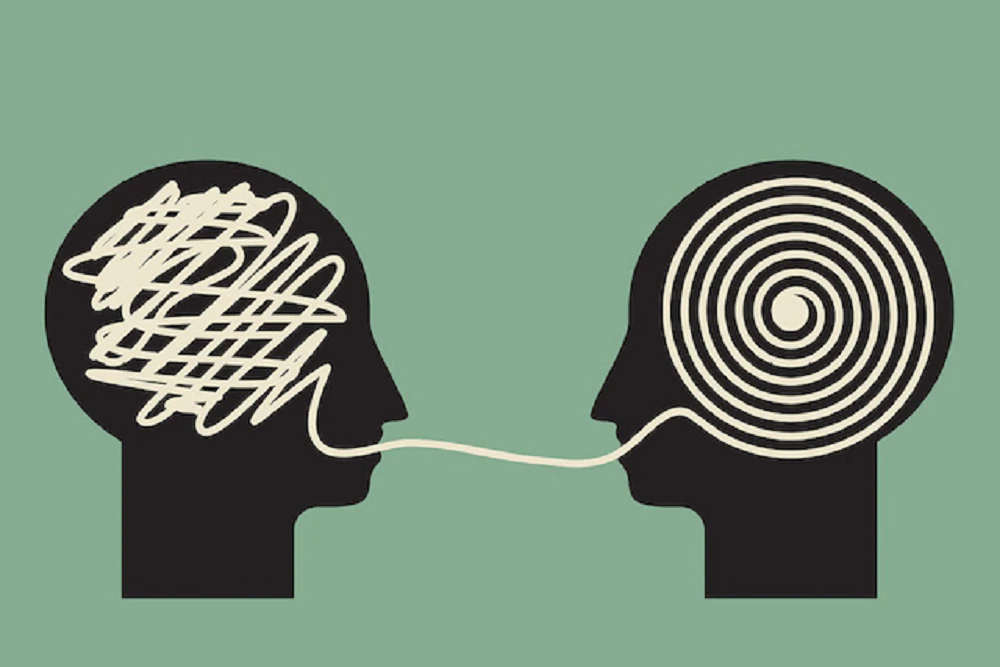
时空间隔
很多人从时空间隔来理解解释的可能性。时空的间隔增加了解释的可能性,这是个事实,但是不适当地表述这一事实就会造成一种错误的指示,仿佛作品的意思本来是挺确定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不那么确定了,于是需要去猜。这样理解时空间隔,作品本身就成了被动消极的东西,时空间隔的增加其实也成了纯粹消极的因素:作品放在那里,不管它是伟大的作品而是贫瘠的作品,随着时间流逝,解释的可能性就会自动增加。解释到头来无非是说:我们不怎么吃得准了,因此可以比较任意地加以解释了。按照同样的思路,写得越晦涩乃至越杂乱的东西就越有解释头了。
作品一旦成了被动的东西,那就怎么解释都行了。而这正是眼下流行的庸俗解释学的主张。但若解释的可能性不是随着时空间隔被动增加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解释的可能性是蕴含在作品之中的。不过得当心,“包含可能性”是一个狡猾的用语。不像糖纸里包一块糖,虽然包含可能性,可能性仍然不在那里,不现成在那里。不在那里怎么包含?(所以,说“蕴含”要好一点。)
解释的理论要点在于,解释始终是文本约束的(text-bound),但作品却并非始终是环境依赖的(situation-dependent)。这和很多解释理论明称的或默认的东西相反,它们主张作品始终依赖于其所从出的处境,因此,为了说明解释的广阔可能性,它们就不得不哪怕违乎本愿地放弃文本对解释的严格约束。
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作品的丰富性本来就是指意蕴的可能性,而主要不是谈所涉及的事情广泛。)我们不妨说伟大作品表现了永恒人性,可惜这个说法多半时候充当的是错误的路标,似乎永恒人性是藏在人性深处现成不变的东西,伟大作品的跨时代性来自某种现成呆板的一致性。与此相反相成的说法是,每一次爱每一次恨都是具体的、特殊的。这里无法展开对这些空泛说法的分析。要之,一个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的孤零零的事实一点都不具体。一个独特的形态主要不在于它独特,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形态或成象,蕴含着需要修炼慧心才能加以理解的东西。经典作品中蕴含了某种异质的、然而经过努力可以理解的意蕴。两个世界的呆板的一致、没发生变化的东西,保证了平庸作品的持续的可理解性,但恰恰不蕴含新颖理解的可能性。
那这岂不是说,作品一问世,就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吗?正是,作品在当时代就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即使在当时,慧眼如脂砚斋者知道《石头记》是传世之作,自明如司马迁者知道他的著作可以传诸后人。不过,当时代的读者倾向于从一个特定情境出发来理解作品。每一种特定阅读都会遮蔽作品的可能空间。特别是作品的当代阅读,因为这时作品刚刚被阅读,还没有形成一个解释传统。正是在这里,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利科说,解释的本质在于让文本中的可能因素“通过解释者创造性地实现出来”。这话不错。当代好说“创造性的解释”,然而,怎么就创造了,这一点始终未见明示。在当代情境中阐发一个文本不仅是文本的诸种可能性之一得到了落实。“创造性”的解释的优秀处在于,它在落实一种意义的同时仍然保持着文本的活力,保持着意蕴的丰富性。解释的难处在于:在展开作品的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保持整个作品的丰富性。我们去补《红楼梦》后三十回四十回,怎么都补不成。(在这里,补写和解释关系十分紧密。)补写不成,这当然不是因为《红楼梦》里的人物特点模糊。相反,他们各个性情鲜明。麻烦在于人事的意蕴丰富。补写不在于落实一种可能性——这太容易了,前八十回越是富有发展的可能性,补写要落实一种可能性就越容易。补写的全部难处在于无论“落实”哪一种可能性,都要求保持前八十回的那种丰富意义。
“创造性的解释”还是解释,不是脱离了文本的创造。面对意蕴丰富的作品,后世的解释者享有广阔的解释空间,但这一空间仍然是受文本约束的,解释是严格的,不仅在训诂层面上如此,在意义层面上仍然如此,虽然严格性并不意味着唯一性。原作本来就向着某些特定的可能世界开放,在这些不同的世界中具有意义。解释的空间是作品创造的,最伟大的东西是属于作品的,而不是属于解释者和读者的。我们这个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怜兮兮想借一种愚蠢的解释理论来为自己赢回一点自尊心。
解释的基础在于学习、理解。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人们谈到“文本的现代解释”的时候经常忘掉了这一点。不少新儒家事先掌握好了一套现代理念,他们从这套现代理念出发来评判儒家经典中哪些内容应当保存、发扬,哪些内容已经过时、应当抛弃。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摆到了儒学的保护者的地位上去了。在我看,保护文化传统是文化部和旅游部的工作。学者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理解、批判让新思想出现。如果中国经典真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对这些经典的理解才能达到某种有意义的结论,而不是已经有了结论再来去伪存真。比较一下这些学者对待中国经典的姿态和西方学者对待西方经典的姿态,一定会很有启发。

















